作者介绍
黛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是麻省理工学院KSJP项目负责人,Undark杂志出版人。布卢姆于1992年赢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她还为《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探索》《健康》《当今心理学》《琼斯妈妈》《卫报》等多家报社撰写科学调研类文章。她曾担任国家科学作家协会会长,现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成员和国家科学院的终生顾问。其他著作包括《猴子的战争》(The Monkey Wars)《头脑中的性别》(Sex on the Brain)《下毒者手册》(The Poisoner’s Handbook)等。
内容介绍
在《试毒小组》一书中,黛博拉•布卢姆为读者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为争取食品安全立法,为完善食品监管,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的发起者和引领者是站在消费者一边的化学家哈维•威利。威利原本在普渡大学任教,于1883年被农业部任命为首席化学家。此后,威利就推动该机构有条不紊地调查食品和饮料欺诈行为,调查涵盖了从黄油、香料到葡萄酒和啤酒等五花八门的食品饮料,对美国食品供应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有些内容骇人听闻。为了测验添加剂的危害性,威利甚至招募志愿者,在农业部化学局进行人体试验,因此被称作“试毒小组”,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威利对食品和饮料的调查以及对这些危害人身行为的批评谴责,既激怒了食品制造商,也惊动了那些极具商业头脑的监管者们。尽管饱受压力,但他拒绝停止研究,哪怕其所得出的结论让强大的公司和政治利益方蒙羞。在呼吁纯净食品的运动中,正是通过以威利为首的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美国首部《纯净食品药品法》才得以诞生。威利等人的不屈抗争,则无愧于消费者保护这场漫长战役的先驱称号,而至今,这场战役仍然没有结束。
19世纪末,美国的食物变得愈加危险甚至致命。牛奶和肉类常用甲醛来保存,而后者通常用于尸体防腐;啤酒和葡萄酒用水杨酸来保存,那是一种药用化学物质;罐装蔬菜用硫酸铜来绿化保鲜,可它本身是一种有毒的金属盐;腐臭的黄油经由硼砂处理可以继续食用,而后者本来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清洁用品。食品制造商则明目张胆出售有害产品,却不会受到监管,也无需接受检查,在他们眼里,利润比顾客的健康更为重要。
为检验这些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危害,为推动食品安全立法,为完善食品监管,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农业部化学家哈维·威利进行“试毒小组”试验,领导了长达30年的食品安全征战,本书讲述了这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还原了一段几乎已被遗忘的历史。有两个因素促使我们认真阅读这本书,一是食品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它不分国界,关系到我们每个的切身利益,了解食品监管的历史至关重要;二是威利的故事具有普遍性,惠及公众的一项改革事业要想成功,是极为艰难的,威利遇到的阻碍,遭遇的挫折,收获的支持,取得的成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既昭示未来,也给后继者以经验和启发。
今时今世,在我们眼里,先祖们的食物上往往笼罩着浪漫的光圈。在如此美好的瑰色中,我们也许想象着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们吃着——且只吃——农场里青翠欲滴的瓜果蔬菜和牧场上食草放养的牲畜家禽,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塑造强健体格。我们甚至可能认为,那时的食物饮品纯属天然,当今这种用化学进行改良、欺世惑众的食物制造手段彼时尚未问世。
这一点,我们都错了。
事实上,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国内售卖的多种食品饮料已经声名狼藉,难以令人信任,有时甚至置人于危境。
牛奶便是很好的例子。奶牛场主们,特别是19世纪向美国拥挤繁华的城市供应牛奶的商人们,知晓可以通过脱脂或者掺水的方式获利。标准做法是在牛奶脱脂后,往每夸脱牛奶中加一品脱温水(译者注:1夸脱=2品脱),这种混合液体呈现浅蓝色。为改善外观,牛奶生产商学会了添加增白剂,如熟石灰或者白垩(译者注:粉笔的主要成分)。有时,他们添加一勺黑糖蜜,使液体偏金黄,呈奶油色。为了模仿液体表面应该出现的奶油层,他们最后可能还会细细浇注一些淡黄色的东西,间或是浓稠的小牛脑浆。
“警察哪去了?”纽约记者约翰·穆拉利质询道,在1853年出版的《纽约及周边区域的牛奶贸易》(The Milk Trade in New York and Vicinity)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这一类——甚至更糟的——制作方法。其证据出自医生们的报告,他们灰心沮丧,直言在纽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肮脏污浊(细菌滋生)且有意为之的牛奶。他的控诉有点戏剧化——尽管他和很多人都义愤填膺、一心求变,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这种掺假行为是非法的。穆拉利还是继续质问:什么时候住手呢?
造假和掺假在其他美国产品中也大行其道。“蜂蜜”通常是增稠的有色玉米糖浆,而“香草”汁则是酒精和综合食用色素的混合物;将草籽混入捣碎的苹果皮酱液,染红并加糖,“草莓”果酱就制成了。“咖啡”主要成分可能是木屑,或小麦、豆类、甜菜、豌豆和蒲公英的种子,它们被烧成焦黑再经研磨就足够以假乱真了。盛有“胡椒”、“肉桂”或“肉豆蔻”的容器中经常被加入更低廉的充数材料,如椰子壳粉、烧焦的绳子,偶尔夹杂地上的垃圾。“面粉”通常以碎石或石膏作为廉价的添加剂。碾碎的昆虫可以混入红糖,往往难以被人察觉——它们的使用常会导致“杂货痒”(译者注:一种经常接触面粉和糖引起的手部皮炎),令人极其不舒服。
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学的兴起——也为食品供应带来了许多新的化学添加剂和合成化合物。食品和饮料制造商仍然不受政府法规管束,无须通过基本安全测试,甚至不用在标签上标注成分,他们因而热情地拥抱新材料,将它们混进食物在食品杂货店售卖,有时这些食品是致命的。最受欢迎的牛奶(它在缺乏有效制冷的时代非常容易腐烂变质)防腐剂——甲醛,其使用灵感源于殡仪馆最新的防腐实践。加工商采用甲醛溶液——标上温良无害的名字如“储存剂”(Preservaline)进行售卖——浸泡腐烂的肉类以去味。其他受欢迎的防腐剂包括水杨酸(一种药用化合物)和硼砂(一种以矿物为主的材料,作为清洁产品而广为人知)。
食品制造商也采用提炼自煤炭副产品的新型合成染料,使原本黯淡无光的产品诱惑力大增。他们找到了廉价的合成化合物,可以作为替代品秘密添加进食物和饮料——糖精来代替糖;醋酸代替柠檬汁;实验室制造的醇类或者酒精,经过染色和调味,摇身一变成为陈年威士忌和优质葡萄酒。正如威斯康星州进步党(译者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上掀起了进步主义运动,其中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领导的进步运动,堪称各州进步运动的典范。)参议员罗伯特·马恩斯·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在1886年所描述的那样:“聪明才智携手阴谋诡计,复合制造出新物质进行食物制假。造出看起来像、吃起来像、闻起来也像,但就是与真货本质迥异的东西;并挂羊头卖狗肉,欺骗买家。”
难怪,当惊恐不安的民众开始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来制止这种欺诈欺骗行为时,他们是高举“纯净化”的大旗行动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纯净食品运动”的十字军战士,不仅在努力净化被污染的食品供应链,而且在努力清理一个腐烂到根源的体系(有政客因亲善该行业而出手进行保护)。正如穆拉利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新的十字军队伍——由科学家、记者、州卫生官员和妇女团体领导者们组成——强烈谴责他们国家的政府居然愿意让这种腐败行径延续下去。
“纯净食品运动”的领导者们一致认为监管监督是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法。他们曾多次看到,美国国内的食品加工商和制造商们对于保护食品供应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责任感,尤其当承担责任可能会威胁其利润时。例如,甲醛已经会直接导致死亡——特别是不少孩子死于饮用所谓的防腐牛奶——生产者却毫无所动,继续使用该防腐剂。防腐剂在避免牛奶变质方面的确非常有用——否则牛奶是难以卖出去的——因此,难以舍弃。
当时美国公司已经多次成功阻止了多方试图通过食品安全立法(哪怕是最温和的立法)的努力。这尤其激怒了那些倡导保护消费者安全的人,因为此时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措施保障食品安全;一些在美国能随心所欲销售的食品饮料现在被其他国家查禁了。与美国同行不同,欧洲啤酒和葡萄酒生产商是不允许在这些饮品中添加危险防腐剂的(哪怕他们可以将这些添加剂加入售往美国的产品中)。
在1898年于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全美纯净食品和药物大会”上,代表们指出,自从大约13年前拉福莱特在参议院发言以来,美国食品行业中的欺诈行为猖獗不休。如果不制定相关政策或计划来处理工业化的食品,这个国家还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当然,有位代表满怀希望地表示,“这个伟大的国家(最终必须)在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护其国民。”
在参会的数百名纯净食品倡议者中,许多人在这看似不太可能产生英雄事迹的地方和人物身上,看到事情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小型化学单位及其首席科学家——一位在哈佛大学接受化学专业培训的中年印第安纳州土著。
但实际上,那是明智之选。
在美国联邦政府考虑创建类似于食品药品管理局之类机构之前的数十年,农业部(1862年由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设立)的任务是分析国内食品和饮料的成分。它是唯一开展这项工作的机构,旨在回应某些农夫的诉求,他们因人工制造食品削弱了其市场而深感不悦。19世纪70年代,来自明尼苏达州农业协会的一份投诉要求该部门调查“科学的错误应用,如给臭鸡蛋除臭、把酸腐黄油去味和将豌豆染绿等”。
但直到1883年农业部任命哈维·华盛顿·威利〔他原本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任教〕为首席化学家后,该机构才开始有条不紊地调查食品和饮料欺诈行为。尽管威利是知名糖化学专家,但他在印第安纳州时就研究过食品制假,并警告过,“假冒”产品对公众健康会产生威胁。抵达农业部后,他立即开展一系列调查,涵盖了从黄油、香料到葡萄酒和啤酒等五花八门的食品饮料,对美国食品供应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有些内容骇人听闻。这些报告促使他于20世纪初在志愿者身上进行人体试验,检测部分最可疑的化学添加剂,这一系列试验被美国报纸称为“试毒小组”研究。
威利对食品和饮料的调查——以及调查结果中的翔实批评——既激怒了制造商,也惊动了那些极具商业头脑的监管者。尽管饱受压力,但他拒绝停止研究。正如纯净食品拥护者们钦佩地指出,威利——及其研究人员——坚持自己的研究,哪怕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让强大的公司和政治利益方蒙羞。
在这些利益方看来,更糟糕的是,他公布了调查结果。威利坚定地向政府官员和立法者,以及广大公众——包括纯净食品运动人士——通报调查结果。他告知国会某委员会,多年来的研究结果使他确信,礼貌地退让是不可接受的。
无论如何,威利总会脱颖而出。他个头高大,身形魁梧,黑头发黑眼睛,私下里幽默迷人,公共场合时而威严,时而夸张。他将成为20世纪之交全美食品安全监管之战中最闻名遐迩的人物,他建立起一个消费者保护联盟,面对预想中的挫折时集结并号召他们坚持抗争。威利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食品安全化学家,但他对这项事业的最大贡献——甚至超越了他所从事和监管的科学任务,甚至还超出了他能令此项事业引人注目的能力——是“他卓绝的指挥才能”,公共卫生历史学家奥斯卡·安德森·小威利(Oscar Anderson Jr Wiley)写道,并补充说:“他是一个领导者,始终保持全局观”,即强烈的消费者保护意识这一长远目标。
威利也有他的不足之处。作为一个业余牧师的儿子,他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自己同盟的要求而站上道德高地。面对敌意,他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也常常拒绝妥协。因为烘焙食品中的有毒化合物,他与人争吵,因为标签上的图片,也吵得一样凶。哪怕在吹毛求疵时,他也未能释放善意,这使他的同盟关系紧绷。有些人认为,这降低了他行动上的有效性。而这点他自己也清楚。
威利自己认为,他未能为他的国家实现一种无畏而严厉的监管保护,这种保护才是他孜孜以求的。他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自己曾独自挺立在——有时甚至败于——反对公司干预法案的斗争中。对于自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190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纯净食品药品法》的通过并生效,他进行了自我批判,这很可能削弱了我们对其成就的感知,并让大家低估了其做出的伟大贡献。
要是那样,我们就又错了。
是的,我们现在依然在为纯净食品而战。但是,请大家认识到,我们已经从19世纪食物、饮料和药品全然不受管制的恐怖境地中走出来,跋涉了漫漫长路。在当下,当商业利益方——就像在威利所处的时代那样——抱怨政府过度干预并宣称取消监管的必要性时,我们要记住,威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为我们奠定了基石,使我们能抵抗住各种压力。他改变了我们的监管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食品、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看法。
也许这并不能总是帮助我们给过去的岁月——甚至那时的英雄们——镀上一层瑰色光辉。但我们应该谨记且不可忘却早期在保护我们国家和个人时所经历的那些教训。当我们回顾全美消费者保护战役中的首场战斗时,我们最好记住它有多么激烈。这是一个引人注目且极富启发意义的故事——它照亮我们脚下的路——故事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说的《纯净食品药品法》,曾经被全美上下称为《威利博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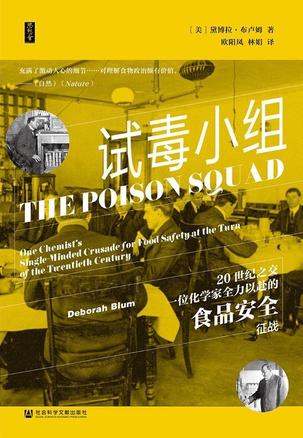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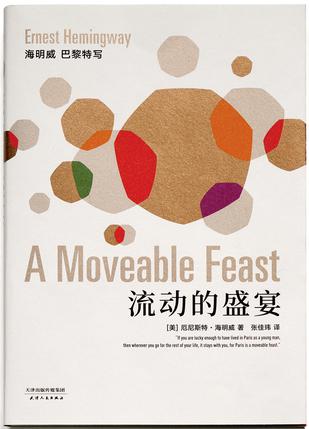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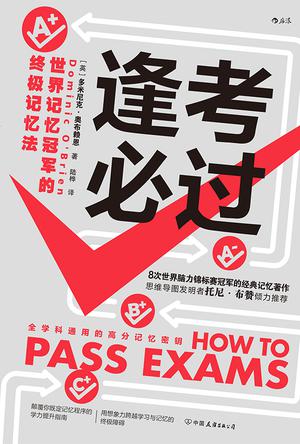





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